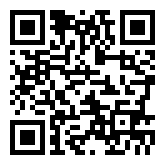序
很早就想把这些故事写下来,但却一直没有动笔。一是手懒,二是担心披露他人的隐私,时过多年,和几个朋友提起,大家都认为我应该写,于是就有了创作的源泉。
Shelter,我不知应该选哪个词最合适,就直译为避护所吧。在美国,没有类似中国的妇联似的组织,但在美国各地都有为妇女儿童设立的各种援助机构,这些机构大多是非营利性的,各州还有免费服务热线以及各种协调机构,这些机构一般是收留受各种虐待的或是无家可归的女人、孩子。
我最先接触到Shelter是在许多年前的圣诞节期间。我当时工作的公司举办“Adopt A Family”的活动,我当时不太理解这个活动的意义,为了凑趣就参加了。“Adopt A Family”是美国一个非常普遍而平常的一个活动,是圣诞节节日期间的一个必然活动。一过了感恩节,公司就会和当地的非营利的慈善机构联系,从那里拿来一大张名单,上面登记着许多家庭和他们在节日里所需要的东西,公司的各部门自愿组合,自由选择一个家庭,然后就筹集这个家庭里需要的东西,一般无非是些家庭用品,衣服鞋子,学艺用品,玩具等,待筹备完毕,就约定一个时间把这些东西送到这个家庭去,当一把圣诞老人。劳拉是当地一个非营利机构的执行总监,也是我们这个活动的协调人,通过这个活动,我和劳拉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,在她的熏陶下,我开始了我的义工生涯,许多年下来,类似的活动不知参加了多少,由此,也接触到了Shelter里的女人。
以下的题材就是根据那些女人的经历而创作的,算是小说吧。第一次以这样的形式贴出来,希望大家多指正。
Sara
1.
每个人都是瘾君子,能不能成瘾,只在于人的自制力。
每个人都有自虐症,能不能成为自虐狂,也在于人的自制力。
第一次打我的人不是我现在的这个又干又瘦,脸白的像个吊死鬼的男朋友,打我的人是我那个一天到晚总是穿着一身西服的律师爸爸。在我十一岁的时候他和我妈妈离了婚,一夜之间,妈妈搬走了一切她能搬走的东西,唯一没被搬走的就是我。至于他们为什么离婚,我从来没有问过,只是从那一夜起,我的童话世界,就如门厅里的那个大花罐子一样,被彻底粉碎了。
我现在这个男朋友是我闲逛时,在市中心的一个画廊里认识的。市中心靠着河边的密西根大街上,除了有各式各样的饭店和酒吧之外,就是有这样那样的画廊,每个画廊都不大,却集居着不少的画家,有名的和没名的。我爸爸的律师事务所就在旁边的另一条街上,以前,爸爸领我去他的事务所,知道我喜欢画画,就把我领到这条街上他的一个客户的画廊里,可我不喜欢那个人的画,却喜欢上了这条街。爸爸妈妈离婚后,爸爸一个案子一个案子的接,放学后的我不愿意回到那个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去,就跑到这条街上闲逛,于是就认识了这个朋友。
他比我大十几岁,个子不高,人瘦瘦的,大概是整天呆在画室里画画,一双手又细又白,不像是男人的手。那时,他挂着一脸的大胡子,满头都是像黑人式的小辫子,冷一看,还以为他是个老黑。他的画廊的橱窗里摆了一幅画,一条小溪,扭扭曲曲地伸向无知的远方。不知道为什么,我就走进了他的画廊。我爱看他作画,他的画里有一种我说不出来的东西。他很少说话,也不撵我走,我就也拿起画笔瞎画,他看了,还在我的画上描上两笔,只有这一两笔,我的画就有神了。
不久的一个周末,我正坐在阳台上发愣,一个大卡车开进了院子,爸爸走过去和司机说了些什么,于是,一伙人就开始往房子里搬东西。待大卡车搬空了,我家的房子里就变了样,也变了味道,我从楼上走下来,好像走错了家门,走进了一个陌生的地方。一个星期后,爸爸就结婚了。按照离婚协议,我每年要在规定的时间里去我妈妈那里。爸爸要去度蜜月,于是要我提前去我妈妈那边。在电话里,为了这事,爸爸把他能用的法律语言都用上了,最后还是把能找到的诅咒的词汇都用上了,才和妈妈达成协议。
爸爸把我送上了飞机,一切手续都和航空公司办好了,我背我的背包,拿着我的画板飞向我妈妈在的城市。下了飞机,航空公司的人把我送到机场出口,我却没有看到我妈妈,航空公司的人就按照爸爸留下的登记表上的电话联系我妈妈,我坐在椅子上等着,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不知过了多久,我被妈妈叫醒,我就跟着拽着行李箱的妈妈上了她的车。一路上,妈妈咬着嘴,没说话。
妈妈的新家是在远郊的一个公寓里,公寓里的东西都是新的,从原来家里搬走的那些东西在这里一样也看不到,也不知妈妈把它们放到了哪里。进了屋,妈妈问我饿不饿。一路上虽然没在飞机上吃什么,可肚子胀胀的,我就摇了摇头,妈妈就让我去洗澡。洗了澡,换上了睡衣,我走进妈妈的房间,把脸埋在被子里,好像能闻到妈妈的味道,很快我就睡着了。
“他这是违反离婚协议,他在我没同意的情况下,在非规定时间里给孩子买了机票,托航空公司就把孩子送了过来,他自己却去度蜜月了,有他这样的人吗?按照协议,他必须赔偿。。。”外屋传来了妈妈的声音,一高一低地进入了我的耳里,我心里酸酸的,拉过被子,蒙住了脑袋。
一年以后,妈妈从公寓里搬到了一个大房子里去,比爸爸的房子还要大,她也结婚了。尽管爸爸有对我的抚养权,可我见他的时间几乎很少,每天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学校里,或者和朋友们在一起,一直到很晚才回家,一进家门我就直接关在自己的屋子里,和爸爸常常是一个星期也说不上一句话。每次去妈妈那里,我看不惯妈妈和她的新丈夫的亲热腻歪样子,而妈妈为了迎合我,更是为了显示她的新的幸福生活,我们每每花在游船上的时间要比在她的新房子里的时间多得多。就是在这样的日子了,我在规定的或是非规定的时间里穿行在爸爸和妈妈的两个家里,随着我的无定性的流动,无数张支票也在他们两个人之间飞来飞去。而就在这样的日子里,我进入了高中。
暑假里,爸爸带我去了纽约,去了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,带我去见了他的朋友们。按照他们的讲法,我只要通过了SAT考试,进入哥大是没什么问题的。而我倒是希望能够离开家,住到学校里去,任何学校都行。
明天就是一年一次的SAT考试的日子了。说实话,我是非常聪明的,虽不用功,可我却从没为学习犯过愁。这天晚上,关在自己的房间里,我却无名地烦躁起来,无意识中,我拿起了画板。这个画板还是我的那位画廊朋友送给我的。要说是送,其实也算不上,因为他没说过送的,只是觉得我用它特别顺手,无形中它就是我的了。有一段时间没有去画廊了,但是这个画板还是我难以离弃的,唯有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画板上,我的心才能够平静下来。
我的脑海里出现了挂在画廊橱窗里的那副扭来扭去的小溪的画,它到底通向何方?这些年里,我从来没有问过他,他为什么要画这样的一幅画?我的画板上也出现了一条小路,可它却不是我意识里的那个样子,画来画去好像还是没有应该有的灵感,要是他在就好了,他可以在我的画上描上两笔,就能把那缥缈的灵感画出来。我的这条小路又能通向何方?
“你怎么还不下来,校车马上就到了,别等着我开车送你,我今天还得出庭呢”。咚咚咚的敲门声伴随着爸爸的大嗓门,我浑身打了个激灵。“校车?”猛一抬头,外面已是大亮,抓起手机一看,哇,七点了。我连忙从地上拾起了书包跑下楼去。
SAT考试持续了五个小时,懵懵懂懂中回到了家,一脑袋扎在床上昏睡了过去。一阵关门声和吵吵嚷嚷的声音把我吵醒了,从床上爬起来,才发现自己是抱着画板睡着的,睡眼朦胧地走下楼去,和正在走进门的爸爸打了个正面。
“你看你这个样子,吊儿郎当地,没事抱个画板干什么?别让我知道你的SAT没考好,去不了哥大,你也向你那个妈一样找个有钱的老男人把自己嫁了。”
劈头盖脸地无故挨了爸爸的一顿骂,也不问我SAT考的如何,我真的很窝火,冲着爸爸喊道:“你喊什么呀,你出庭不利找我发什么火呀。我妈找有钱的老男人,你身边的那个女人不也是找了你这个有钱的老男人了吗?”
啪,爸爸的大巴掌扇到我的脸上,原本就是晕乎乎的我,更没有预料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,此刻是金星满天乱舞,摇摇晃晃地从楼梯上滚到了地上,滚到了爸爸的脚下,胸腔一阵尖痛,让我没了呼吸。
“你还和我顶嘴,还敢这么说你妈,你这个垃圾,我他妈的是白养你了,”噗,一脚踢在我的后腰上,又一脚踢开随我滚到地上的画板,“你他妈的给我滚!”又是一脚,还不解恨,又猛地抓起画板就朝火炉里扔了过去,吼道:“滚!!”
(待续)

 , 长工慢了一步
, 长工慢了一步 



 , 这样对女儿
, 这样对女儿 
 实上的加工
实上的加工